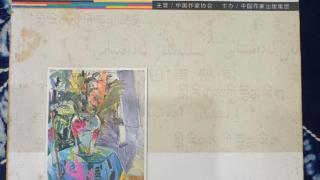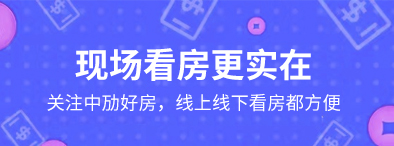西班牙女作家蒙特罗曾说,“小说家要追寻内心的潜意识,去挖掘现实之下自己都不曾发觉的自我。”侗族女作家杨芳兰面对女性潜意识世界,以女性视角,将女性潜意识予以物化,在作品中将女性人物丰盈的精神面向予以呈现。
杨芳兰现在居住在榕江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她的创作经历颇具戏剧性。2002年,她辞去工作,在榕江县老客车站开起了烟酒店。2012年的某一天,因为学校要求写日记而儿子抵触,杨芳兰便安慰儿子说:“写日记没什么难的,咱们一起写。”于是,杨芳兰从2012年开始,便和儿子一同写起了日记。2013年她开始写散文,创作小说。她把写好的散文、小说一篇篇上传到QQ空间分享,逐渐受到关注,她的中篇小说《滨江花园》在2015年第3期《民族文学》发表 。这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,她一边做生意一边写作,陆续在《安徽文学》《长江丛刊》《滇池》等刊物发表中、短篇小说几十篇。
杨芳兰中篇小说《滨江花园》在2015年第3期《民族文学》发表。
杨芳兰在农村生活过,现在榕江县城生活,她从2015年第3期《民族文学》发表的《滨江花园》到2024年《辽河》刊发的《冬至之约》,从小说中的“熬村”到“榕城”,杨芳兰的系列中、短篇小说,叙事半径在城与乡,着力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叙写,呈现小说中人物的百炼钢与绕指柔。小说体现出作家对女性生存空间的关怀与悲悯,展示了女性在乡土情怀中的坚守与传承,展现了女性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如何坚韧地活出自我、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朝向。
她的第一篇中篇小说《滨江花园》,聚焦生存和婚姻关系问题,书写城市男女难以言说的情感隐痛。围绕筹钱买房产生系列冲突,贷款、卖寿木,夫妻吵闹直至离婚。小说以“买房”为故事引线,呈现了中年夫妇无力、无奈的生存和情感状态,刻画了作为妻子的“我”的自立自强精神。
中国自古有“鱼跃龙门”从而改变身份、处境的追求向往,杨芳兰的小说《跃龙门》,借助于日常生活细节的繁密呈现,讲述了一个进城人员明珠的家庭悲剧故事。“我”从熬村来到榕城,在不知做什么的情况下,铤而走险。找到一些小钱的明珠志不在此,后来单干,卖小百货。又与刘老师产生感情,准备结婚,不料因卷入非法集资受骗,新房被砸烂、被洗劫一空,明珠也受了重伤。《跃龙门》通过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充满温情的写作风格,展示了进城人员一心想改变身份和命运的悲欢交织的生活,并特别关注他们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世界。
小说《蔑匠街》刊发于2018年第6期《民族文学》。
人们往往把精神寄托于一物或一事,《长在天边的树》写的是一个精神寄托物“树”消失的故事。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的李大树,回乡连续三年参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考未果,决定外出打工。不料几个月后又回家来了,准备到熬村小学当代课老师。大树看到别人卖掉山林得到大笔钱吃酒吃肉时,也嚷着叫父母卖掉杉树换钱,母亲杨婄更坚决反对砍自己视为“守寨树”的自留山的杉树。后来李大树在打工时患上的尿毒症病发,手里无钱的母亲只能砍树卖钱治病。至此,“熬村一棵杉树都没有了。”母亲杨婄更的精神寄托也没有了。这里,树的存在就是杨婄更的精神存在与精神幻象。《春江水暖》同样是一个把精神寄托在“物”身上的故事。李鸭客在犀牛潭养鸭,看到一对鸳鸯带着几个小鸳鸯自由自在地在水中畅游,李鸭客对鸳鸯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,并发誓要保护好犀牛潭的鸳鸯。与李鸭客关系暧昧的在村委会旁边开小卖部的女子陈秀琴,她的弟弟陈秀松好吃懒做,准备去犀牛潭抓鸳鸯卖。小说中,人与鸳鸯相望相守,李鸭客与陈秀琴的情感书写,在与周边人现实遭际的连接和亲近中,同时赢得了生活世界的宽度,探究了他们的精神岩层。
《牛霸一方》多角度表现新时代榕城社会生活变革中人的精神变化,小说以改革前至今榕城社会变革为大背景,以失业人员杨美和她的丈夫刘雄、儿子刘牛为重心,在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矛盾中展开广阔的命运故事,用文学揭示了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书写社会转型期普通人创造新生活的坚定意志,具有浓郁的榕城生活气息。《牛霸一方》是一部家庭烹饪史。小说描写、刻画了一些与乡村还未完全挣断关系的城市人,以及他们身经的苦恼、烦忧、孤寂而不屈的精神状态。
杨芳兰中篇小说《牛霸一方》刊发于《民族文学》2023年第五期。
一些地方的农村,年轻女性的名字不能上老人的墓碑,《请叫我孙桂兰》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沉重的故事。母亲从湖南远嫁到榕城一个“远在天边的”的村庄——熬村,奶奶死后墓碑上没有刻上母亲的名字。“凡是嫁进熬村的女子,不管她如何孝敬公婆,公婆去世后,墓碑依然不能刻上孝媳的姓名。”奶奶的墓碑没有自己的名字,母亲忍了,爷爷死后母亲的名字再没有刻在墓碑上,母亲不忍了。母亲认为自己不被当作一家人,毅然决定外出打工。也许这也是一种文化冲突,母亲是湖南嫁来的汉族女子,文化习俗与熬村当然不一样。小说演绎了一个自强独立的现代乡村女性的故事,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,相对深入地书写了乡村女性的命运的荒寒与深邃,探索了女性复杂的精神世界。
当今中国社会,已迈入老龄化。《挂在树梢的黄叶》是一部紧跟时代热点、贴近生活现场、关注老年人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。婆婆去世后,成天泡在药罐子里、患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的八十岁家公由谁人照料成了问题:随意大小便,弄得家里到处臭烘烘;无人照看时还自己出门乱走,不知去向。家人不胜其烦。吴倩在一家康养院听到有一种镇静剂,便买了些回家,放在家公拿不到的地方。然而,吴倩还来不及给家公吃,看似什么都不知道的家公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偷吃了几粒镇静剂,永远地睡了过去。小说以沉重的笔调,描写了一曲家庭伦理悲歌。让人们思索个人工作与传统美德之间,在面对严峻现实,传统美德如何得以传承?
总之,杨芳兰的系列中、短篇小说,在对家庭生活与伦理关系的描摹中,人情、人性中的普遍性和幽微感得以精准显现。她关注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精神面向,是她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特征。借助小说,从传统道德和价值的坚固堡垒里,她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新一代女性的自立、自强的精神朝向。
(作者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,黔东南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文/李茂奎
编辑/刘立超
二审/姚曼
三审/黄蔚